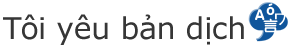- Văn bản
- Lịch sử
根据第九表,可知自宋至明,政府岁人钱数越来越少,银数则越来越多。由此我
根据第九表,可知自宋至明,政府岁人钱数越来越少,银数则越来越多。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明代社会“用银而废钱”的趋势。
银在明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之所以远过于钱,原因有种种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为明代商业的特别发展。明自立国以后,随着国家的长期统一.人口与物产都大量增加,从而促进商业的空前繁荣。[28]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由于大规模商业的经营,“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在今安徽南部),江北则山右(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Z.–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29]。当商业发展,交易量增大的时候,用价值低下的铜钱来做交换媒介自然要感到不便,故有行使价值较大的银两[30]之必要。
在明代流通的货币中,银两之所以比铜钱重要得多,又由于当日铸钱量的减小。铜是铸钱的主要原料,可是经过过去长期的开采以后,明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间或有之,随取随竭”[31]。铜矿生产既然有限,明初政府因为铸钱需铜,“令私铸钱作废铜送官,偿以钱。是时有司责民出铜,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32]。由于铜的缺乏,明代铜价昂贵,从而铸钱成本特别的高[33],故铸钱数量甚小。根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则例,当时除南京外,全国各地的炉座,一年共可铸钱一八九、四一四贯零八百文。[34]这和北宋熙宁六年(1073)后及元丰三年(1080)每年约铸钱六百万贯[35]的数字比较起来,约只为后者的百分之三多点。不特如此,洪武二十六年所规定的每年18、19万贯的铸钱额,实际上并不是年年铸造,而是时常停铸。就是在铸造的年头,也不一定按照定额铸造。因此,明朝到16世纪末为止的两百多年间,铸钱的数目并不多,总共恐怕不过千把万贯。[36]换句话说,明代头二百多年所铸的钱,在北宋熙宁(1067—1077)、元丰(1078—1085)时代铸钱最多的年头,只要两三年的时间便可铸造出来。钱的铸造额既然这样稀少,不足以满足当日在商业发展中的市场上的需要,人们自然要普遍用银来交易了。
除由于商业发展及铸钱量小以外,明代社会对于银的需要所以远比钱大,又由于钱值不如银值那么稳定。关于铜钱的流通情况,顾炎武说:“我朝(明朝)钱法,遇改元即随年号各铸造通用。”[37]因此,明代某一皇帝死了,上面刻有他的年号的钱便不再通用,从而价值下跌,或打折扣才能行使,使持有人大受损失。[38]自然,由于铸钱的稀少,全国各地不可能都使用刻有当今皇帝年号的钱,也有使用宋代及其他朝代旧钱的。可是,旧钱有许多种,无论哪一种都不能长期行用;当停止行用以后,钱值往往下落三分之二,即低跌到只等于原值的三分之一。[39]由于钱值的剧烈波动,人民生活自不免要大受打击。例如隆庆四年(1570)高拱说:“小民日求升合,觅数钱以度朝夕,必是钱法有一定之说,乃可彼此通行。而乃旦更暮改,迄无定议。小民见得如此.恐今日得钱而明日不用,将必至于饿死。是以愈变更愈纷乱,愈禁约愈惊惶,铺面不敢开,买卖不得行,而嗷嗷为甚。”[40]因此,明代钱值老是不稳定的结果,人民为着保护自己的利益,自然不愿用钱,而普遍采用价值比较稳定的银两来作货币了。
五
综括上文,我们可知以银表示的物价,自宋至明,有向下降落的趋势。我们因此可以测量出明代白银的购买力,约为宋、元时代的两倍左右。
在这几个世纪内,中国白银的购买力所以增大,原因有种种的不同,但在货币方面对于白银需要的激增,当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明代商业发展声中,由于通货膨胀而不断贬值的纸币,和供给不足、价值低下而不稳定的铜钱,都不足以满足各地市场上对于货币的庞大需要,故银两便普遍流通起来。除市场交易以外,面对着这种货币经济发展的大潮流,政府原来以征收实物为主的税收,也改为“折银”,更助长对银需要的增大。上文说过,早在正统元年(1436),政府在长江以南大部分运输困难地区课征的田赋,已开始由米、麦改折成银,按照每石折银二钱五分的比率来征收,称为“金花银”。这种课征办法,后来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更扩大范围,使全国各地(除漕粮地区外)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摊派,都合并在一起,改折成银两来缴纳,称为“一条鞭法”。[41]此外,在盐法方面,明代政府初时实行“开中”(去声,纳粟中盐的意思)之法,即由商人在边地(以北方及西北为主)开垦耕种,把收获的粟或米向沿边驻军缴纳来作军饷,然后换取盐引,前往淮南等产盐地区领盐出售。可是自弘治五年(1492)开始,政府改变这种办法,不再要商人纳粟或米,而要他们纳银,然后给与盐引。[42]因此,明代政府岁人中的银两,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对于因银的需要增大而物价下落及银的购买力提高的情形,生当明季的黄梨洲已经有一个敏锐的观察,他说:“至今日而赋税市易,银乃单行……夫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于何所?故田土之价,不当异时之十一。岂其壤瘠与?曰否,不能为赋税也。百货之价,亦不当异时之十一。岂其物阜与?曰否,市易无资也。”([43]这种因银的需要激增而购买力提高的背景,说明了明朝中叶以后,当世界新航路发现的浪潮冲击到中国海岸来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在对外贸易扩展的过程中,要长期自国外输入大量的银子。
注释:
[1]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曰文本,东洋文库论丛第六,东京,大正十五年,即1926年)第一分册,第二、三章。又参考拙著《从货币制度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论集》(台北,1953年)第一集,页117—123。
[2]拙著《元代的纸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集刊》)第十五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页1—48。
[3] Emma Helen Blair and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eds.,The PhiEppine Islands.1493—1898(以下简称PAil Isls.),Cleveland,1903—09,Vo1.29,PP.70—71;T’oung Pa0,V01.Vl,Leide,1895,PP.457—458;China Review,Vo1.XIX,no.4,Shanghai,1891.PP.243—255.
[4] Phil.Isls.,V01.19,P.237;V01.27,PP.64—65.William Lytle Schurz,The Manila Galleon,New York,1939,PP.405—6.
[5] Lien.sheng Yang,Money and Gredit in China:A Short History,Cambridge,1952, pp.47—48.
[6]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道光十四年刊)卷一一,页12—l3,“黄金”。按文中说洪武八年的金银比价,见《大明会典》(中文书局影印万历十五年司礼监刊本)卷三一,页1,“钞法”;洪武十八年,见同书卷二九,页1,“征收”;洪武三十年,见同书卷二九,页3,“征收”。
[7]参考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8),页503及619;Lien—Sheng Yang,前引书,页47—48;A.Kobata,“The Production and Uses of Gold and Silver in Sixtecnth-and Sev emeenth-Century Japan,”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Second Series,Vo1.XVIIl,No.2,Au gust l965,PP,245—266.
[8]正统五年(1440)山西大同的金价,便宜到每两只值银一两六厘七分少点(据“金六钱折银一两”计算出来),和其他年代的金价比较起来,着实过于偏低。按《明英宗实录》卷六五,页1,载正统五年三月“乙丑,巡抚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左侍郎于谦奏:山西民已贫困,所解大同折粮金、银诸物,甚不易得。近闻彼处巡抚官以金、银成色不及,抑令煎销,不惟延候日久,且所用木炭、黑铅等物,并亏折之数,何从出办。乞令银一两折米二石,金六钱折银一两,收库支用,则民免稽延,不悮农种,官军亦得其便。上谓户部臣曰:谦所言良是,其速行之!”按明代政府在山西大同一带驻有不少军队来巩固国防,为着应付那里军费的开支,故命令山西民众向大同缴解折粮金、银,而规定“银一两折米二石,金六钱折银一两”。这种比率,显然是根据当地市场实况(或行情)来斟酌决定的。现在我们要问,当日山西大同的金价为什么会低落到这样的程度?我想,这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根据上面引文提及“山西……大同……巡抚官以金、银成色不及,抑令煎销”一事,当时在那里的黄金的成色,可能远较白银为低。第二,由于当日山西北部社会经济的特殊情况,金、银的供求状况,可能各有不同。换句话说,比较起来,金可能供过于求,银可能求过于供,故产生金价偏低的特殊现象。
[9]宋、明时代长江下游或江南米价的变动,大致可以代表全国米价变动的趋势,因为这个地区在当日全国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关于此点,除因为自宋以来“苏(州)、常(州)熟,天下足”的长江三角洲是全国的谷仓以外,我们又可以从这个地区的户口在全国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之大,观察出来。北宋元丰三年(1080)全国共有一六、四七二、九二○户,其中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路共有五、五四四、四五二户(加藤繁《支那经济史考证》,东京,1953,下卷,页347—348),约占全国产数的百分之三四。及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共有一○、六五二、七八九户,六○、五四五、八一二口,其中江苏、浙江、安徽及江西共有五、六○五、○一一户,三○、二二五、九八六口(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c,1959,P.10),约占全国总额的百分之五○。
[10]明代绢价所以特别下降,除由于如本文将要指出的货币方面的原因以外,又由于明初政府在各地积极增加蚕桑生产,发展丝纺织业。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吴晗曾经加以研究,他说:“龙凤十一年(1365)六月,下令凡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照比例递加。地方官亲自督视,不执行命令的处罚。不种桑的使出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出麻布或棉布一匹。(《明太祖实录》卷一五,《明史}卷一三八《杨思义传》)洪武元年(1368),把这制度推广到全国,并规定科征之类,……栽桑的四年以后再征租。……二十五年(1392),令凤阳、滁州、庐州、和州每户种桑二百株……令天下卫所屯田军士每人种桑百株……二十七年(1394),令户部教天下百姓务要多种桑、枣和棉花,并教以种植之法。每一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遣充军。……二十九年(1396),以湖广诸郡宜于种桑,而种之者少,命于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种二十石,派人送到辰、沅、靖、全、道、永、宝庆、衡州等处(今湖南及广西北部一带),各给一石,使其民种之,发展这一地区蚕丝生产和丝织工业(《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五,二二二,二三二,二四三,《明会典》,朱国桢《大政记》,《明通纪》)。为了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下诏指出农桑为衣食之本,全国地方官考课,一定要报告农桑的成绩,并规定二十六年(1393)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不论多少,郡免征赋(《明太祖实录》卷七七,二四三,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出版社出版《历史研究》,1955,第3期,页58)。由于蚕丝增产政策的积极推行,明代绢产量自然增加,生产成本自然下降,故绢价远较宋代为低。除此以外,自元代开始,由于黄道婆在松江普遍传授棉纺织技术,棉纺织工业在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发展起来(拙著《鸦片战爭前江苏的棉纺织业》,《清华学报》新一卷第三期,1958年,页25—51)。到了明代,许多人都用棉布缝制衣服,对于绢的需要自然减小,故绢价下降。
[11]拙著《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集刊》第十本,页193—222;《元代的纸币》,见前。
[12] 《大明会典》卷三一,页1,《钞法》;《明史》(艺文印书馆本)卷八一,页1—2,《食货志》;《明史稿》,志六二,页15,《食货》四。
[13] 《明史稿》,志六二,页15,《食货》四。
[14]例如《明太宗实录》(史语所印)卷三三,页8,载永乐二年(1404)七月庚寅,“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言:比岁钞法不通,皆缘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明史》卷八一,页3,《食货志》略同)又《明史》卷八一,页4,《食货志》说:“及(仁宗)即位(1425),以钞不行,询(户部尚书夏)原吉。原吉言:钞多则轻,少则重。民间钞不行,缘散多敛少。……”
[15] 《续文献通考》卷一○,页5—6,在洪武二十七年项下说:“时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初以钞一贯折钱五十文,后折百六十文。浙、闽、江(西)、(两)广诸处皆然。由是物价踊贵,钞法益坏不行。”又参考《明太祖实录》(史语所印)卷二三四,页2,“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明史》卷八一,页3,《食货志》;《明史稿》,志六二,页16,《食货》四。
[16] 《明史》卷八一,
银在明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之所以远过于钱,原因有种种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为明代商业的特别发展。明自立国以后,随着国家的长期统一.人口与物产都大量增加,从而促进商业的空前繁荣。[28]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由于大规模商业的经营,“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在今安徽南部),江北则山右(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Z.–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29]。当商业发展,交易量增大的时候,用价值低下的铜钱来做交换媒介自然要感到不便,故有行使价值较大的银两[30]之必要。
在明代流通的货币中,银两之所以比铜钱重要得多,又由于当日铸钱量的减小。铜是铸钱的主要原料,可是经过过去长期的开采以后,明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间或有之,随取随竭”[31]。铜矿生产既然有限,明初政府因为铸钱需铜,“令私铸钱作废铜送官,偿以钱。是时有司责民出铜,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32]。由于铜的缺乏,明代铜价昂贵,从而铸钱成本特别的高[33],故铸钱数量甚小。根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则例,当时除南京外,全国各地的炉座,一年共可铸钱一八九、四一四贯零八百文。[34]这和北宋熙宁六年(1073)后及元丰三年(1080)每年约铸钱六百万贯[35]的数字比较起来,约只为后者的百分之三多点。不特如此,洪武二十六年所规定的每年18、19万贯的铸钱额,实际上并不是年年铸造,而是时常停铸。就是在铸造的年头,也不一定按照定额铸造。因此,明朝到16世纪末为止的两百多年间,铸钱的数目并不多,总共恐怕不过千把万贯。[36]换句话说,明代头二百多年所铸的钱,在北宋熙宁(1067—1077)、元丰(1078—1085)时代铸钱最多的年头,只要两三年的时间便可铸造出来。钱的铸造额既然这样稀少,不足以满足当日在商业发展中的市场上的需要,人们自然要普遍用银来交易了。
除由于商业发展及铸钱量小以外,明代社会对于银的需要所以远比钱大,又由于钱值不如银值那么稳定。关于铜钱的流通情况,顾炎武说:“我朝(明朝)钱法,遇改元即随年号各铸造通用。”[37]因此,明代某一皇帝死了,上面刻有他的年号的钱便不再通用,从而价值下跌,或打折扣才能行使,使持有人大受损失。[38]自然,由于铸钱的稀少,全国各地不可能都使用刻有当今皇帝年号的钱,也有使用宋代及其他朝代旧钱的。可是,旧钱有许多种,无论哪一种都不能长期行用;当停止行用以后,钱值往往下落三分之二,即低跌到只等于原值的三分之一。[39]由于钱值的剧烈波动,人民生活自不免要大受打击。例如隆庆四年(1570)高拱说:“小民日求升合,觅数钱以度朝夕,必是钱法有一定之说,乃可彼此通行。而乃旦更暮改,迄无定议。小民见得如此.恐今日得钱而明日不用,将必至于饿死。是以愈变更愈纷乱,愈禁约愈惊惶,铺面不敢开,买卖不得行,而嗷嗷为甚。”[40]因此,明代钱值老是不稳定的结果,人民为着保护自己的利益,自然不愿用钱,而普遍采用价值比较稳定的银两来作货币了。
五
综括上文,我们可知以银表示的物价,自宋至明,有向下降落的趋势。我们因此可以测量出明代白银的购买力,约为宋、元时代的两倍左右。
在这几个世纪内,中国白银的购买力所以增大,原因有种种的不同,但在货币方面对于白银需要的激增,当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明代商业发展声中,由于通货膨胀而不断贬值的纸币,和供给不足、价值低下而不稳定的铜钱,都不足以满足各地市场上对于货币的庞大需要,故银两便普遍流通起来。除市场交易以外,面对着这种货币经济发展的大潮流,政府原来以征收实物为主的税收,也改为“折银”,更助长对银需要的增大。上文说过,早在正统元年(1436),政府在长江以南大部分运输困难地区课征的田赋,已开始由米、麦改折成银,按照每石折银二钱五分的比率来征收,称为“金花银”。这种课征办法,后来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更扩大范围,使全国各地(除漕粮地区外)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摊派,都合并在一起,改折成银两来缴纳,称为“一条鞭法”。[41]此外,在盐法方面,明代政府初时实行“开中”(去声,纳粟中盐的意思)之法,即由商人在边地(以北方及西北为主)开垦耕种,把收获的粟或米向沿边驻军缴纳来作军饷,然后换取盐引,前往淮南等产盐地区领盐出售。可是自弘治五年(1492)开始,政府改变这种办法,不再要商人纳粟或米,而要他们纳银,然后给与盐引。[42]因此,明代政府岁人中的银两,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对于因银的需要增大而物价下落及银的购买力提高的情形,生当明季的黄梨洲已经有一个敏锐的观察,他说:“至今日而赋税市易,银乃单行……夫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于何所?故田土之价,不当异时之十一。岂其壤瘠与?曰否,不能为赋税也。百货之价,亦不当异时之十一。岂其物阜与?曰否,市易无资也。”([43]这种因银的需要激增而购买力提高的背景,说明了明朝中叶以后,当世界新航路发现的浪潮冲击到中国海岸来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在对外贸易扩展的过程中,要长期自国外输入大量的银子。
注释:
[1]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曰文本,东洋文库论丛第六,东京,大正十五年,即1926年)第一分册,第二、三章。又参考拙著《从货币制度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论集》(台北,1953年)第一集,页117—123。
[2]拙著《元代的纸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集刊》)第十五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页1—48。
[3] Emma Helen Blair and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eds.,The PhiEppine Islands.1493—1898(以下简称PAil Isls.),Cleveland,1903—09,Vo1.29,PP.70—71;T’oung Pa0,V01.Vl,Leide,1895,PP.457—458;China Review,Vo1.XIX,no.4,Shanghai,1891.PP.243—255.
[4] Phil.Isls.,V01.19,P.237;V01.27,PP.64—65.William Lytle Schurz,The Manila Galleon,New York,1939,PP.405—6.
[5] Lien.sheng Yang,Money and Gredit in China:A Short History,Cambridge,1952, pp.47—48.
[6]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道光十四年刊)卷一一,页12—l3,“黄金”。按文中说洪武八年的金银比价,见《大明会典》(中文书局影印万历十五年司礼监刊本)卷三一,页1,“钞法”;洪武十八年,见同书卷二九,页1,“征收”;洪武三十年,见同书卷二九,页3,“征收”。
[7]参考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8),页503及619;Lien—Sheng Yang,前引书,页47—48;A.Kobata,“The Production and Uses of Gold and Silver in Sixtecnth-and Sev emeenth-Century Japan,”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Second Series,Vo1.XVIIl,No.2,Au gust l965,PP,245—266.
[8]正统五年(1440)山西大同的金价,便宜到每两只值银一两六厘七分少点(据“金六钱折银一两”计算出来),和其他年代的金价比较起来,着实过于偏低。按《明英宗实录》卷六五,页1,载正统五年三月“乙丑,巡抚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左侍郎于谦奏:山西民已贫困,所解大同折粮金、银诸物,甚不易得。近闻彼处巡抚官以金、银成色不及,抑令煎销,不惟延候日久,且所用木炭、黑铅等物,并亏折之数,何从出办。乞令银一两折米二石,金六钱折银一两,收库支用,则民免稽延,不悮农种,官军亦得其便。上谓户部臣曰:谦所言良是,其速行之!”按明代政府在山西大同一带驻有不少军队来巩固国防,为着应付那里军费的开支,故命令山西民众向大同缴解折粮金、银,而规定“银一两折米二石,金六钱折银一两”。这种比率,显然是根据当地市场实况(或行情)来斟酌决定的。现在我们要问,当日山西大同的金价为什么会低落到这样的程度?我想,这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根据上面引文提及“山西……大同……巡抚官以金、银成色不及,抑令煎销”一事,当时在那里的黄金的成色,可能远较白银为低。第二,由于当日山西北部社会经济的特殊情况,金、银的供求状况,可能各有不同。换句话说,比较起来,金可能供过于求,银可能求过于供,故产生金价偏低的特殊现象。
[9]宋、明时代长江下游或江南米价的变动,大致可以代表全国米价变动的趋势,因为这个地区在当日全国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关于此点,除因为自宋以来“苏(州)、常(州)熟,天下足”的长江三角洲是全国的谷仓以外,我们又可以从这个地区的户口在全国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之大,观察出来。北宋元丰三年(1080)全国共有一六、四七二、九二○户,其中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路共有五、五四四、四五二户(加藤繁《支那经济史考证》,东京,1953,下卷,页347—348),约占全国产数的百分之三四。及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共有一○、六五二、七八九户,六○、五四五、八一二口,其中江苏、浙江、安徽及江西共有五、六○五、○一一户,三○、二二五、九八六口(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c,1959,P.10),约占全国总额的百分之五○。
[10]明代绢价所以特别下降,除由于如本文将要指出的货币方面的原因以外,又由于明初政府在各地积极增加蚕桑生产,发展丝纺织业。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吴晗曾经加以研究,他说:“龙凤十一年(1365)六月,下令凡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照比例递加。地方官亲自督视,不执行命令的处罚。不种桑的使出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出麻布或棉布一匹。(《明太祖实录》卷一五,《明史}卷一三八《杨思义传》)洪武元年(1368),把这制度推广到全国,并规定科征之类,……栽桑的四年以后再征租。……二十五年(1392),令凤阳、滁州、庐州、和州每户种桑二百株……令天下卫所屯田军士每人种桑百株……二十七年(1394),令户部教天下百姓务要多种桑、枣和棉花,并教以种植之法。每一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遣充军。……二十九年(1396),以湖广诸郡宜于种桑,而种之者少,命于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种二十石,派人送到辰、沅、靖、全、道、永、宝庆、衡州等处(今湖南及广西北部一带),各给一石,使其民种之,发展这一地区蚕丝生产和丝织工业(《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五,二二二,二三二,二四三,《明会典》,朱国桢《大政记》,《明通纪》)。为了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下诏指出农桑为衣食之本,全国地方官考课,一定要报告农桑的成绩,并规定二十六年(1393)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不论多少,郡免征赋(《明太祖实录》卷七七,二四三,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出版社出版《历史研究》,1955,第3期,页58)。由于蚕丝增产政策的积极推行,明代绢产量自然增加,生产成本自然下降,故绢价远较宋代为低。除此以外,自元代开始,由于黄道婆在松江普遍传授棉纺织技术,棉纺织工业在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发展起来(拙著《鸦片战爭前江苏的棉纺织业》,《清华学报》新一卷第三期,1958年,页25—51)。到了明代,许多人都用棉布缝制衣服,对于绢的需要自然减小,故绢价下降。
[11]拙著《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集刊》第十本,页193—222;《元代的纸币》,见前。
[12] 《大明会典》卷三一,页1,《钞法》;《明史》(艺文印书馆本)卷八一,页1—2,《食货志》;《明史稿》,志六二,页15,《食货》四。
[13] 《明史稿》,志六二,页15,《食货》四。
[14]例如《明太宗实录》(史语所印)卷三三,页8,载永乐二年(1404)七月庚寅,“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言:比岁钞法不通,皆缘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明史》卷八一,页3,《食货志》略同)又《明史》卷八一,页4,《食货志》说:“及(仁宗)即位(1425),以钞不行,询(户部尚书夏)原吉。原吉言:钞多则轻,少则重。民间钞不行,缘散多敛少。……”
[15] 《续文献通考》卷一○,页5—6,在洪武二十七年项下说:“时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初以钞一贯折钱五十文,后折百六十文。浙、闽、江(西)、(两)广诸处皆然。由是物价踊贵,钞法益坏不行。”又参考《明太祖实录》(史语所印)卷二三四,页2,“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明史》卷八一,页3,《食货志》;《明史稿》,志六二,页16,《食货》四。
[16] 《明史》卷八一,
0/5000
根据第九表,可知自宋至明,政府岁人钱数越来越少,银数则越来越多。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明代社会“用银而废钱”的趋势。 银在明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之所以远过于钱,原因有种种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为明代商业的特别发展。明自立国以后,随着国家的长期统一.人口与物产都大量增加,从而促进商业的空前繁荣。[28]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由于大规模商业的经营,“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在今安徽南部),江北则山右(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Z.–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29]。当商业发展,交易量增大的时候,用价值低下的铜钱来做交换媒介自然要感到不便,故有行使价值较大的银两[30]之必要。 在明代流通的货币中,银两之所以比铜钱重要得多,又由于当日铸钱量的减小。铜是铸钱的主要原料,可是经过过去长期的开采以后,明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间或有之,随取随竭”[31]。铜矿生产既然有限,明初政府因为铸钱需铜,“令私铸钱作废铜送官,偿以钱。是时有司责民出铜,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32]。由于铜的缺乏,明代铜价昂贵,从而铸钱成本特别的高[33],故铸钱数量甚小。根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则例,当时除南京外,全国各地的炉座,一年共可铸钱一八九、四一四贯零八百文。[34]这和北宋熙宁六年(1073)后及元丰三年(1080)每年约铸钱六百万贯[35]的数字比较起来,约只为后者的百分之三多点。不特如此,洪武二十六年所规定的每年18、19万贯的铸钱额,实际上并不是年年铸造,而是时常停铸。就是在铸造的年头,也不一定按照定额铸造。因此,明朝到16世纪末为止的两百多年间,铸钱的数目并不多,总共恐怕不过千把万贯。[36]换句话说,明代头二百多年所铸的钱,在北宋熙宁(1067—1077)、元丰(1078—1085)时代铸钱最多的年头,只要两三年的时间便可铸造出来。钱的铸造额既然这样稀少,不足以满足当日在商业发展中的市场上的需要,人们自然要普遍用银来交易了。 除由于商业发展及铸钱量小以外,明代社会对于银的需要所以远比钱大,又由于钱值不如银值那么稳定。关于铜钱的流通情况,顾炎武说:“我朝(明朝)钱法,遇改元即随年号各铸造通用。”[37]因此,明代某一皇帝死了,上面刻有他的年号的钱便不再通用,从而价值下跌,或打折扣才能行使,使持有人大受损失。[38]自然,由于铸钱的稀少,全国各地不可能都使用刻有当今皇帝年号的钱,也有使用宋代及其他朝代旧钱的。可是,旧钱有许多种,无论哪一种都不能长期行用;当停止行用以后,钱值往往下落三分之二,即低跌到只等于原值的三分之一。[39]由于钱值的剧烈波动,人民生活自不免要大受打击。例如隆庆四年(1570)高拱说:“小民日求升合,觅数钱以度朝夕,必是钱法有一定之说,乃可彼此通行。而乃旦更暮改,迄无定议。小民见得如此.恐今日得钱而明日不用,将必至于饿死。是以愈变更愈纷乱,愈禁约愈惊惶,铺面不敢开,买卖不得行,而嗷嗷为甚。”[40]因此,明代钱值老是不稳定的结果,人民为着保护自己的利益,自然不愿用钱,而普遍采用价值比较稳定的银两来作货币了。五 综括上文,我们可知以银表示的物价,自宋至明,有向下降落的趋势。我们因此可以测量出明代白银的购买力,约为宋、元时代的两倍左右。 在这几个世纪内,中国白银的购买力所以增大,原因有种种的不同,但在货币方面对于白银需要的激增,当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在明代商业发展声中,由于通货膨胀而不断贬值的纸币,和供给不足、价值低下而不稳定的铜钱,都不足以满足各地市场上对于货币的庞大需要,故银两便普遍流通起来。除市场交易以外,面对着这种货币经济发展的大潮流,政府原来以征收实物为主的税收,也改为“折银”,更助长对银需要的增大。上文说过,早在正统元年(1436),政府在长江以南大部分运输困难地区课征的田赋,已开始由米、麦改折成银,按照每石折银二钱五分的比率来征收,称为“金花银”。这种课征办法,后来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更扩大范围,使全国各地(除漕粮地区外)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摊派,都合并在一起,改折成银两来缴纳,称为“一条鞭法”。[41]此外,在盐法方面,明代政府初时实行“开中”(去声,纳粟中盐的意思)之法,即由商人在边地(以北方及西北为主)开垦耕种,把收获的粟或米向沿边驻军缴纳来作军饷,然后换取盐引,前往淮南等产盐地区领盐出售。可是自弘治五年(1492)开始,政府改变这种办法,不再要商人纳粟或米,而要他们纳银,然后给与盐引。[42]因此,明代政府岁人中的银两,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对于因银的需要增大而物价下落及银的购买力提高的情形,生当明季的黄梨洲已经有一个敏锐的观察,他说:“至今日而赋税市易,银乃单行……夫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于何所?故田土之价,不当异时之十一。岂其壤瘠与?曰否,不能为赋税也。百货之价,亦不当异时之十一。岂其物阜与?曰否,市易无资也。”([43]这种因银的需要激增而购买力提高的背景,说明了明朝中叶以后,当世界新航路发现的浪潮冲击到中国海岸来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在对外贸易扩展的过程中,要长期自国外输入大量的银子。注释:[1]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的研究》(曰文本,东洋文库论丛第六,东京,大正十五年,即1926年)第一分册,第二、三章。又参考拙著《从货币制度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论集》(台北,1953年)第一集,页117—123。[2]拙著《元代的纸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集刊》)第十五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页1—48。[3] Emma Helen Blair and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eds.,The PhiEppine Islands.1493—1898(以下简称PAil Isls.),Cleveland,1903—09,Vo1.29,PP.70—71;T’oung Pa0,V01.Vl,Leide,1895,PP.457—458;China Review,Vo1.XIX,no.4,Shanghai,1891.PP.243—255.
[4] Phil.Isls.,V01.19,P.237;V01.27,PP.64—65.William Lytle Schurz,The Manila Galleon,New York,1939,PP.405—6.
[5] Lien.sheng Yang,Money and Gredit in China:A Short History,Cambridge,1952, pp.47—48.
[6]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道光十四年刊)卷一一,页12—l3,“黄金”。按文中说洪武八年的金银比价,见《大明会典》(中文书局影印万历十五年司礼监刊本)卷三一,页1,“钞法”;洪武十八年,见同书卷二九,页1,“征收”;洪武三十年,见同书卷二九,页3,“征收”。
[7]参考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8),页503及619;Lien—Sheng Yang,前引书,页47—48;A.Kobata,“The Production and Uses of Gold and Silver in Sixtecnth-and Sev emeenth-Century Japan,”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Second Series,Vo1.XVIIl,No.2,Au gust l965,PP,245—266.
[8]正统五年(1440)山西大同的金价,便宜到每两只值银一两六厘七分少点(据“金六钱折银一两”计算出来),和其他年代的金价比较起来,着实过于偏低。按《明英宗实录》卷六五,页1,载正统五年三月“乙丑,巡抚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左侍郎于谦奏:山西民已贫困,所解大同折粮金、银诸物,甚不易得。近闻彼处巡抚官以金、银成色不及,抑令煎销,不惟延候日久,且所用木炭、黑铅等物,并亏折之数,何从出办。乞令银一两折米二石,金六钱折银一两,收库支用,则民免稽延,不悮农种,官军亦得其便。上谓户部臣曰:谦所言良是,其速行之!”按明代政府在山西大同一带驻有不少军队来巩固国防,为着应付那里军费的开支,故命令山西民众向大同缴解折粮金、银,而规定“银一两折米二石,金六钱折银一两”。这种比率,显然是根据当地市场实况(或行情)来斟酌决定的。现在我们要问,当日山西大同的金价为什么会低落到这样的程度?我想,这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根据上面引文提及“山西……大同……巡抚官以金、银成色不及,抑令煎销”一事,当时在那里的黄金的成色,可能远较白银为低。第二,由于当日山西北部社会经济的特殊情况,金、银的供求状况,可能各有不同。换句话说,比较起来,金可能供过于求,银可能求过于供,故产生金价偏低的特殊现象。
[9]宋、明时代长江下游或江南米价的变动,大致可以代表全国米价变动的趋势,因为这个地区在当日全国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关于此点,除因为自宋以来“苏(州)、常(州)熟,天下足”的长江三角洲是全国的谷仓以外,我们又可以从这个地区的户口在全国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之大,观察出来。北宋元丰三年(1080)全国共有一六、四七二、九二○户,其中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路共有五、五四四、四五二户(加藤繁《支那经济史考证》,东京,1953,下卷,页347—348),约占全国产数的百分之三四。及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共有一○、六五二、七八九户,六○、五四五、八一二口,其中江苏、浙江、安徽及江西共有五、六○五、○一一户,三○、二二五、九八六口(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c,1959,P.10),约占全国总额的百分之五○。
[10]明代绢价所以特别下降,除由于如本文将要指出的货币方面的原因以外,又由于明初政府在各地积极增加蚕桑生产,发展丝纺织业。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吴晗曾经加以研究,他说:“龙凤十一年(1365)六月,下令凡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照比例递加。地方官亲自督视,不执行命令的处罚。不种桑的使出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出麻布或棉布一匹。(《明太祖实录》卷一五,《明史}卷一三八《杨思义传》)洪武元年(1368),把这制度推广到全国,并规定科征之类,……栽桑的四年以后再征租。……二十五年(1392),令凤阳、滁州、庐州、和州每户种桑二百株……令天下卫所屯田军士每人种桑百株……二十七年(1394),令户部教天下百姓务要多种桑、枣和棉花,并教以种植之法。每一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遣充军。……二十九年(1396),以湖广诸郡宜于种桑,而种之者少,命于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种二十石,派人送到辰、沅、靖、全、道、永、宝庆、衡州等处(今湖南及广西北部一带),各给一石,使其民种之,发展这一地区蚕丝生产和丝织工业(《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五,二二二,二三二,二四三,《明会典》,朱国桢《大政记》,《明通纪》)。为了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下诏指出农桑为衣食之本,全国地方官考课,一定要报告农桑的成绩,并规定二十六年(1393)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不论多少,郡免征赋(《明太祖实录》卷七七,二四三,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出版社出版《历史研究》,1955,第3期,页58)。由于蚕丝增产政策的积极推行,明代绢产量自然增加,生产成本自然下降,故绢价远较宋代为低。除此以外,自元代开始,由于黄道婆在松江普遍传授棉纺织技术,棉纺织工业在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发展起来(拙著《鸦片战爭前江苏的棉纺织业》,《清华学报》新一卷第三期,1958年,页25—51)。到了明代,许多人都用棉布缝制衣服,对于绢的需要自然减小,故绢价下降。
[11]拙著《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集刊》第十本,页193—222;《元代的纸币》,见前。
[12] 《大明会典》卷三一,页1,《钞法》;《明史》(艺文印书馆本)卷八一,页1—2,《食货志》;《明史稿》,志六二,页15,《食货》四。
[13] 《明史稿》,志六二,页15,《食货》四。
[14]例如《明太宗实录》(史语所印)卷三三,页8,载永乐二年(1404)七月庚寅,“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言:比岁钞法不通,皆缘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明史》卷八一,页3,《食货志》略同)又《明史》卷八一,页4,《食货志》说:“及(仁宗)即位(1425),以钞不行,询(户部尚书夏)原吉。原吉言:钞多则轻,少则重。民间钞不行,缘散多敛少。……”
[15] 《续文献通考》卷一○,页5—6,在洪武二十七年项下说:“时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初以钞一贯折钱五十文,后折百六十文。浙、闽、江(西)、(两)广诸处皆然。由是物价踊贵,钞法益坏不行。”又参考《明太祖实录》(史语所印)卷二三四,页2,“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明史》卷八一,页3,《食货志》;《明史稿》,志六二,页16,《食货》四。
[16] 《明史》卷八一,
[4] Phil.Isls.,V01.19,P.237;V01.27,PP.64—65.William Lytle Schurz,The Manila Galleon,New York,1939,PP.405—6.
[5] Lien.sheng Yang,Money and Gredit in China:A Short History,Cambridge,1952, pp.47—48.
[6]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道光十四年刊)卷一一,页12—l3,“黄金”。按文中说洪武八年的金银比价,见《大明会典》(中文书局影印万历十五年司礼监刊本)卷三一,页1,“钞法”;洪武十八年,见同书卷二九,页1,“征收”;洪武三十年,见同书卷二九,页3,“征收”。
[7]参考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1958),页503及619;Lien—Sheng Yang,前引书,页47—48;A.Kobata,“The Production and Uses of Gold and Silver in Sixtecnth-and Sev emeenth-Century Japan,”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Second Series,Vo1.XVIIl,No.2,Au gust l965,PP,245—266.
[8]正统五年(1440)山西大同的金价,便宜到每两只值银一两六厘七分少点(据“金六钱折银一两”计算出来),和其他年代的金价比较起来,着实过于偏低。按《明英宗实录》卷六五,页1,载正统五年三月“乙丑,巡抚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左侍郎于谦奏:山西民已贫困,所解大同折粮金、银诸物,甚不易得。近闻彼处巡抚官以金、银成色不及,抑令煎销,不惟延候日久,且所用木炭、黑铅等物,并亏折之数,何从出办。乞令银一两折米二石,金六钱折银一两,收库支用,则民免稽延,不悮农种,官军亦得其便。上谓户部臣曰:谦所言良是,其速行之!”按明代政府在山西大同一带驻有不少军队来巩固国防,为着应付那里军费的开支,故命令山西民众向大同缴解折粮金、银,而规定“银一两折米二石,金六钱折银一两”。这种比率,显然是根据当地市场实况(或行情)来斟酌决定的。现在我们要问,当日山西大同的金价为什么会低落到这样的程度?我想,这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根据上面引文提及“山西……大同……巡抚官以金、银成色不及,抑令煎销”一事,当时在那里的黄金的成色,可能远较白银为低。第二,由于当日山西北部社会经济的特殊情况,金、银的供求状况,可能各有不同。换句话说,比较起来,金可能供过于求,银可能求过于供,故产生金价偏低的特殊现象。
[9]宋、明时代长江下游或江南米价的变动,大致可以代表全国米价变动的趋势,因为这个地区在当日全国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关于此点,除因为自宋以来“苏(州)、常(州)熟,天下足”的长江三角洲是全国的谷仓以外,我们又可以从这个地区的户口在全国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之大,观察出来。北宋元丰三年(1080)全国共有一六、四七二、九二○户,其中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路共有五、五四四、四五二户(加藤繁《支那经济史考证》,东京,1953,下卷,页347—348),约占全国产数的百分之三四。及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共有一○、六五二、七八九户,六○、五四五、八一二口,其中江苏、浙江、安徽及江西共有五、六○五、○一一户,三○、二二五、九八六口(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Cambridgc,1959,P.10),约占全国总额的百分之五○。
[10]明代绢价所以特别下降,除由于如本文将要指出的货币方面的原因以外,又由于明初政府在各地积极增加蚕桑生产,发展丝纺织业。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吴晗曾经加以研究,他说:“龙凤十一年(1365)六月,下令凡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照比例递加。地方官亲自督视,不执行命令的处罚。不种桑的使出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出麻布或棉布一匹。(《明太祖实录》卷一五,《明史}卷一三八《杨思义传》)洪武元年(1368),把这制度推广到全国,并规定科征之类,……栽桑的四年以后再征租。……二十五年(1392),令凤阳、滁州、庐州、和州每户种桑二百株……令天下卫所屯田军士每人种桑百株……二十七年(1394),令户部教天下百姓务要多种桑、枣和棉花,并教以种植之法。每一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遣充军。……二十九年(1396),以湖广诸郡宜于种桑,而种之者少,命于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种二十石,派人送到辰、沅、靖、全、道、永、宝庆、衡州等处(今湖南及广西北部一带),各给一石,使其民种之,发展这一地区蚕丝生产和丝织工业(《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五,二二二,二三二,二四三,《明会典》,朱国桢《大政记》,《明通纪》)。为了保证命令的贯彻执行,下诏指出农桑为衣食之本,全国地方官考课,一定要报告农桑的成绩,并规定二十六年(1393)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不论多少,郡免征赋(《明太祖实录》卷七七,二四三,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出版社出版《历史研究》,1955,第3期,页58)。由于蚕丝增产政策的积极推行,明代绢产量自然增加,生产成本自然下降,故绢价远较宋代为低。除此以外,自元代开始,由于黄道婆在松江普遍传授棉纺织技术,棉纺织工业在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发展起来(拙著《鸦片战爭前江苏的棉纺织业》,《清华学报》新一卷第三期,1958年,页25—51)。到了明代,许多人都用棉布缝制衣服,对于绢的需要自然减小,故绢价下降。
[11]拙著《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集刊》第十本,页193—222;《元代的纸币》,见前。
[12] 《大明会典》卷三一,页1,《钞法》;《明史》(艺文印书馆本)卷八一,页1—2,《食货志》;《明史稿》,志六二,页15,《食货》四。
[13] 《明史稿》,志六二,页15,《食货》四。
[14]例如《明太宗实录》(史语所印)卷三三,页8,载永乐二年(1404)七月庚寅,“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言:比岁钞法不通,皆缘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明史》卷八一,页3,《食货志》略同)又《明史》卷八一,页4,《食货志》说:“及(仁宗)即位(1425),以钞不行,询(户部尚书夏)原吉。原吉言:钞多则轻,少则重。民间钞不行,缘散多敛少。……”
[15] 《续文献通考》卷一○,页5—6,在洪武二十七年项下说:“时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初以钞一贯折钱五十文,后折百六十文。浙、闽、江(西)、(两)广诸处皆然。由是物价踊贵,钞法益坏不行。”又参考《明太祖实录》(史语所印)卷二三四,页2,“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明史》卷八一,页3,《食货志》;《明史稿》,志六二,页16,《食货》四。
[16] 《明史》卷八一,
đang được dịch, vui lòng đợi..


Các ngôn ngữ khác
Hỗ trợ công cụ dịch thuật: Albania, Amharic, Anh, Armenia, Azerbaijan, Ba Lan, Ba Tư, Bantu, Basque, Belarus, Bengal, Bosnia, Bulgaria, Bồ Đào Nha, Catalan, Cebuano, Chichewa, Corsi, Creole (Haiti), Croatia, Do Thái, Estonia, Filipino, Frisia, Gael Scotland, Galicia, George, Gujarat, Hausa, Hawaii, Hindi, Hmong, Hungary, Hy Lạp, Hà Lan, Hà Lan (Nam Phi), Hàn, Iceland, Igbo, Ireland, Java, Kannada, Kazakh, Khmer, Kinyarwanda, Klingon, Kurd, Kyrgyz, Latinh, Latvia, Litva, Luxembourg, Lào, Macedonia, Malagasy, Malayalam, Malta, Maori, Marathi, Myanmar, Mã Lai, Mông Cổ, Na Uy, Nepal, Nga, Nhật, Odia (Oriya), Pashto, Pháp, Phát hiện ngôn ngữ, Phần Lan, Punjab, Quốc tế ngữ, Rumani, Samoa, Serbia, Sesotho, Shona, Sindhi, Sinhala, Slovak, Slovenia, Somali, Sunda, Swahili, Séc, Tajik, Tamil, Tatar, Telugu, Thái, Thổ Nhĩ Kỳ, Thụy Điển, Tiếng Indonesia, Tiếng Ý, Trung, Trung (Phồn thể), Turkmen, Tây Ban Nha, Ukraina, Urdu, Uyghur, Uzbek, Việt, Xứ Wales, Yiddish, Yoruba, Zulu, Đan Mạch, Đức, Ả Rập, dịch ngôn ngữ.
- The onCreate( ) method fetches the diffi
- taxi standrunning latedirectionblocknear
- tốc độ tăng trưởng nhanh của các ngành c
- những thứ trên đó
- Tôi đến đó chơi và để chup ảnh
- A SERIOUS PRODUCTIVITY PROBLEM
- describe an item ofthat you use often.yo
- The Directors or any committee of Direct
- trước đây tôi thường đi làm trễ, nhưng g
- The Directors or any committee of Direct
- rất dễ thương
- ban hành quy định quản lý và xét duyệt c
- chiếc xe 45 chỗ màu cam hiện đại, tiện n
- 中国经济史论坛 当前位置:中国经济史论坛 » 中外古今 » 古代通论 » 宋明间
- 망해버린걸까
- 中国经济史论坛 当前位置:中国经济史论坛 » 中外古今 » 古代通论 » 宋明间
- Hiện nay vấn đề vệ sinh an toàn thực phẩ
- 中国经济史论坛 当前位置:中国经济史论坛 » 中外古今 » 古代通论 » 宋明间
- Hiện nay vấn đề vệ sinh an toàn thực phẩ
- 中国经济史论坛 当前位置:中国经济史论坛 » 中外古今 » 古代通论 » 宋明间
- sau đó nó lan rộng ra toàn thế giới
- trước đây tôi thường đi làm trễ
- what colour is your shirt?
- thành phần xã hội